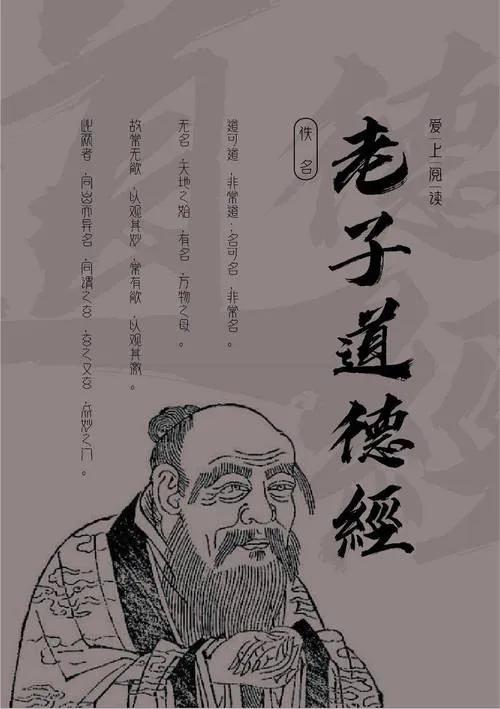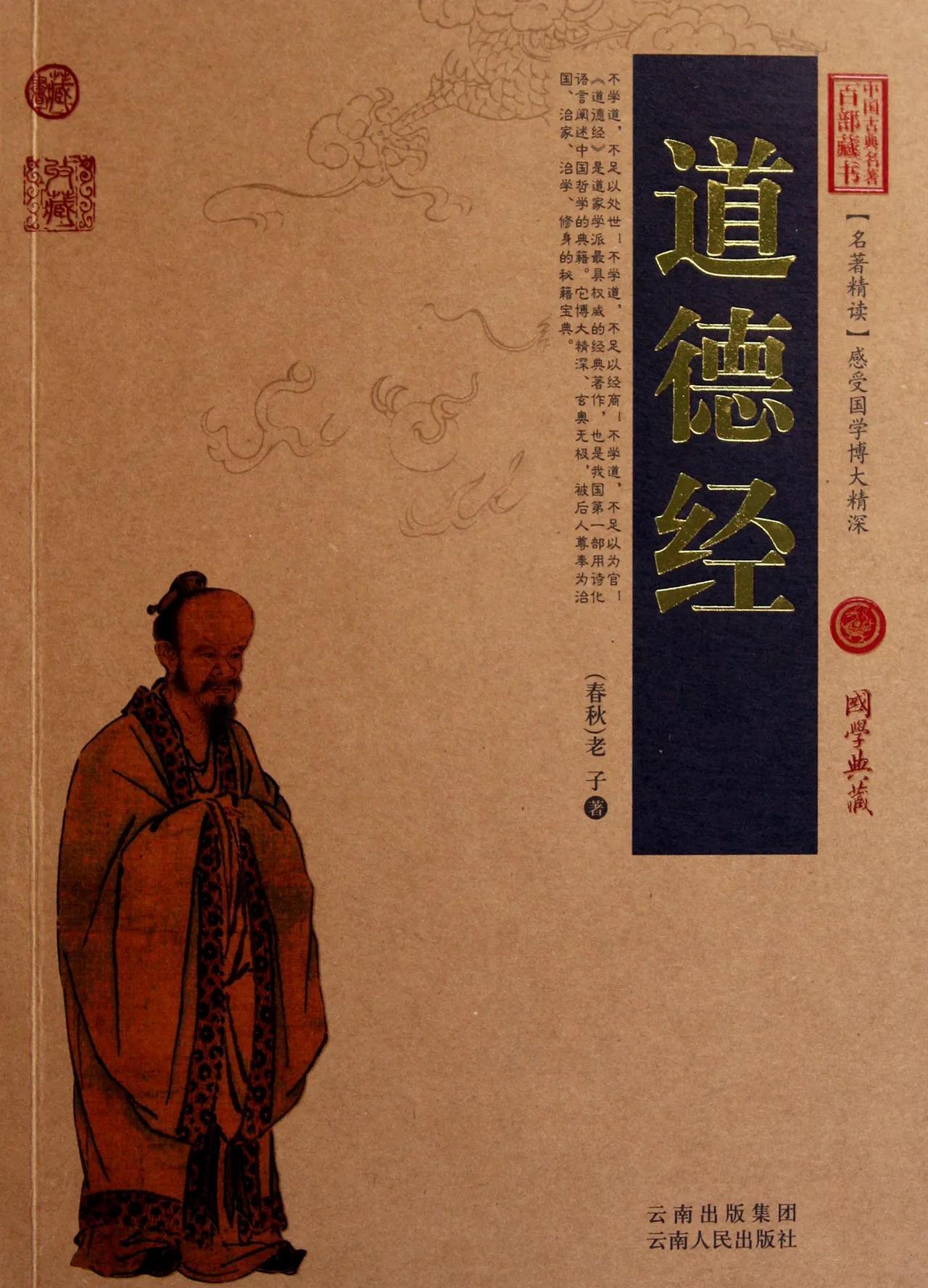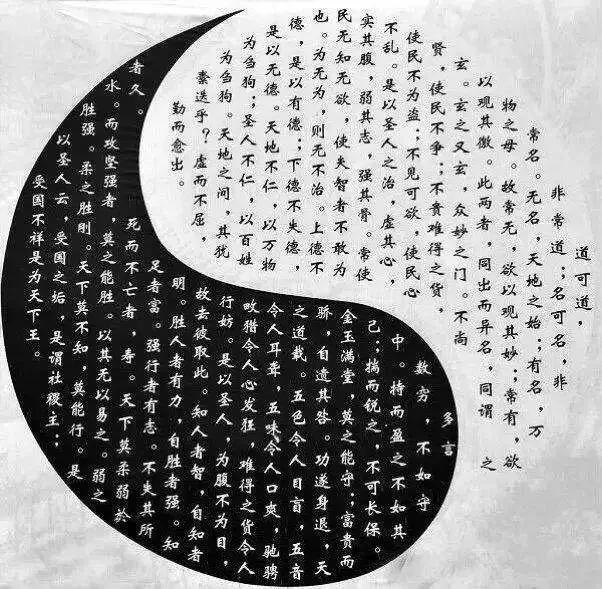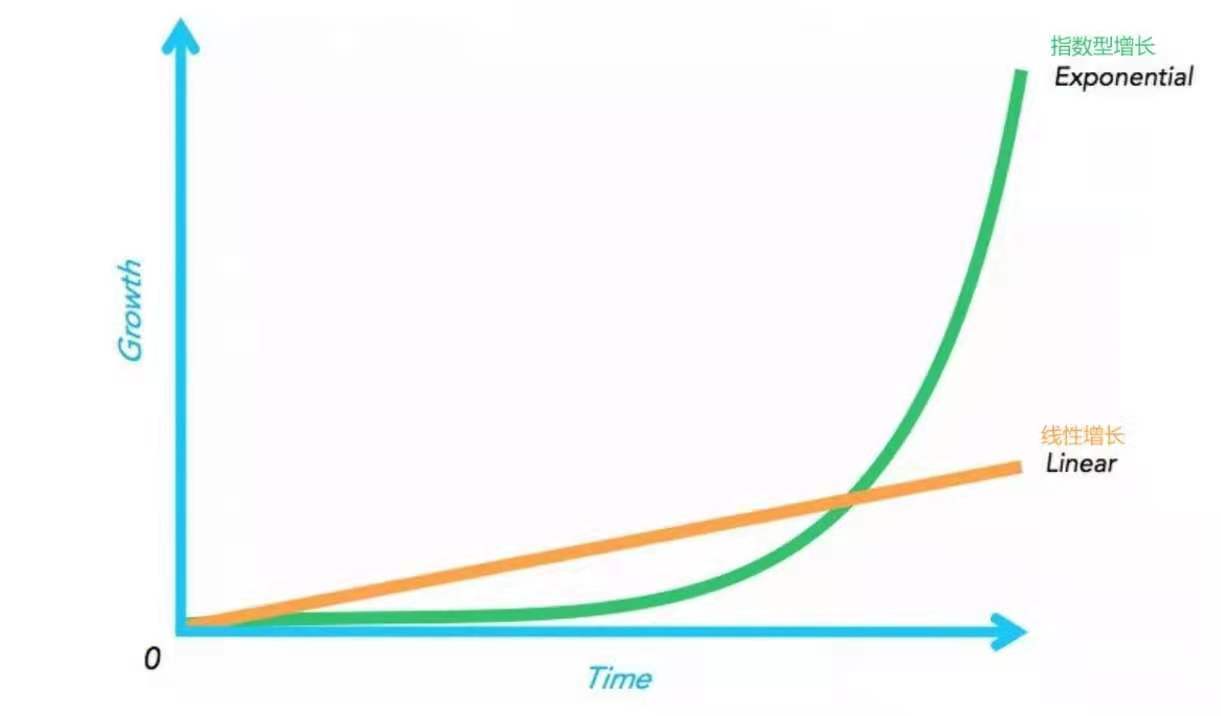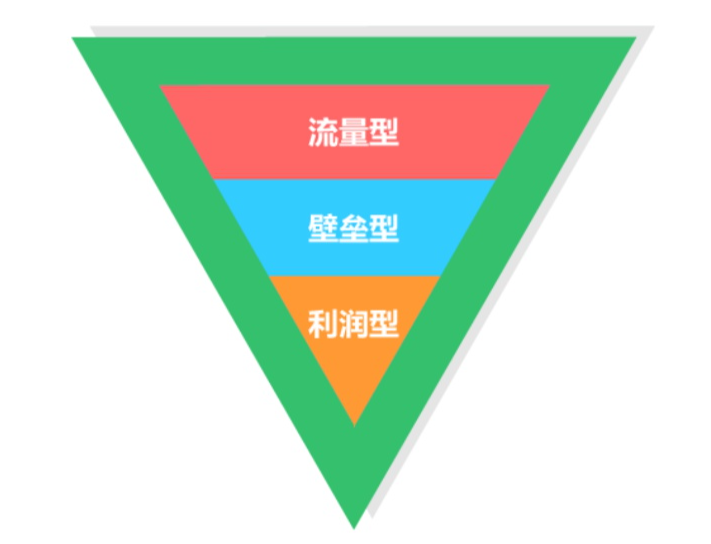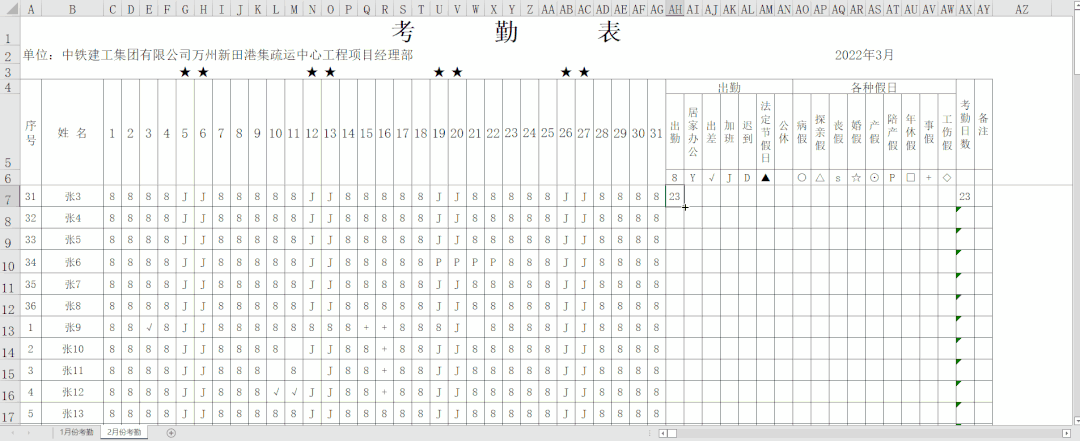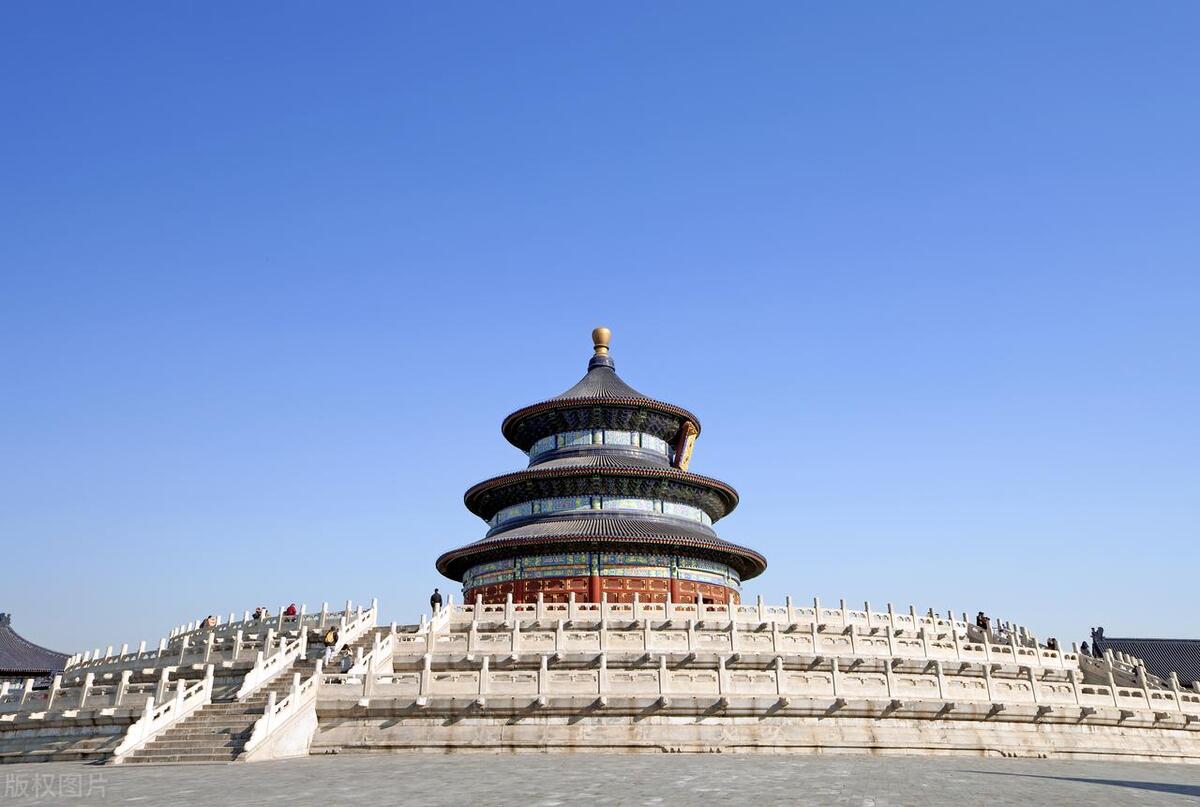对话巫鸿|与记忆有关的生命
巫鸿在芝加哥的家中。
本文作者
贺婧
在不太常见的情况下,阅读一本学者写的书会让我在读着的当下产生关于这本书是如何被写就的想象——是怎样一个人,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哪些具体的场景之中?《豹迹:与记忆有关》却印证了这种情况。作为艺术史学家巫鸿出版的一本回忆性文集,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学者的“真实”生命里,这种生命无关乎任何生平性的记述,因此也就不必要完整甚至准确,它是在记忆的模糊和偏差里生长出来的,裹挟着艺术史学者的行文里特有的视觉暗示,在书页之间缓缓地生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艺术家式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学者、研究者甚或是任何相同层面上的创造者,都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共享着对生命经验的尊重和反思。也是从这里出发,与巫鸿的对谈集中在关于知识与生命、关于一个资深艺术史学者对于艺术作品之原初体验的讨论,它们让人感受到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的智慧,就像学者书房里的那只黑猫,会从芝加哥的清晨跃进我们的屏幕里。
贺婧:H,巫鸿:W
H:新书《豹迹》呈现了与你私人记忆有关的故事,因此和之前出版的所有艺术史研究著作都很不一样。在读到中间“生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发现你对记忆的追溯好像都跟场地和空间有关,比如北海公园、天安门广场、密歇根湖边、普林斯顿树林等等。那么对你来说,记忆的起点是否就是某个“场地”或某种空间化的东西呢?
W:记忆其实就是平常想起件什么事,一般不会太注意,但是后来说要做一本书,或者要把这个事儿再整体地想一想,我就发现自己的记忆主要还是围绕着地点的。但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人就对“事件”特别敏感,他的记忆都围绕着事件、人物和对话,但我发现我的记忆不是这样,也可能和我作为艺术写作者或美术史学家有关,我仔细想了一下我的写作,不管涉及古代还是当代,都与我们说的这个地点、场地有关。场地和空间当然是连着,但是场地好像是有一个明确的地方,比如说我长在后海的胡同里,或者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也都是一些很清楚的地点,这些地点就会先跳出来,然后回忆是围绕着它、一层一层积累下来的,所以地点也生成了一种叙事,它像吸铁石似的将记忆聚集起来。而我在当代艺术的写作里也会特别重视一些特殊的“site”(地点、场所),所以对我来说地点、场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巫鸿在芝加哥家中。
H:是的,一般来说从事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是较少介入当代艺术的现场的,你似乎是一个特例。当我放下《豹迹》再去回看你近年来出版的学术专著的时候——包括《空间的敦煌》《时空中的美术》《重屏》《废墟的故事》《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等等,发现它们其实都跟空间、场所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是否正是因为对于空间、对于人身处其中的真实艺术经验的特别敏感与关注,而使得你的工作能够从古代艺术跨越到当代艺术?因为空间、场所、身体的在场性等都是当代艺术中非常首要的问题。
W:这个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自己的艺术研究中比较重视媒材。《重屏》那本书里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什么是中国古代绘画?”——这好像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原来大家研究绘画往往只研究图像,但我认为绘画这个概念包含了物质性和空间性。所以屏风有前有后有空间,而当你有了前后的时候,人的位置就都出来了,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在我的写作里。《重屏》很早,是1996年的作品,所以后来我觉得从这种空间的、物质性的角度再进入(当代艺术)就非常容易,比如很多当代艺术家也是在特殊的空间去做装置或行为艺术,包括绘画等等,这些都能够把我的东西串在一块儿,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学术研究还是非学术写作,所有这些场地、物质、材料、观看,还有空间,以及人和对象之间相互的这种位置等等,都可以是一体的。
H:所以《豹迹》这本书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能从一种“内部”通道进入到你的研究中,就像从海底隧道里观看一样,而不再仅仅是从外面观望式地理解你的艺术史写作。开篇的同名文章《豹迹》与你在七十年代末在新疆考察石窟的真实经验有关,同时又充满了艺术想象所带来的精神强度,我读完之后很受触动,因为它揭示出一个特别鲜活的艺术观看者和研究者的形象,这个形象饱含了人在艺术和自然面前所能获得的那种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好像某种“初心”。对你来说,这种原初的、富有情感的艺术体验在你长达四十几年的研究生涯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
W:这个其实蛮难回答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很重要,我就从头来说一说。“初心”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无论从事什么事情,尤其在艺术方面可能总是源于一种爱好,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那时候也说不上对美术有什么理解,就是一种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可以很狂热。但是当我们一旦进入学术之途,就好像有一种常规,让你把这种主观的、未经雕琢的个人感觉放在一边,甚至有时候要很有意识地分开。不管是音乐史还是美术史,都是“人文科学”,也就是你要把它们作为一种“科学”去研究,它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历史。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你必须跳出自己,跳出本原的那些想法和很感性的东西,它们当然还可以存在,但是不能让它影响你对历史的价值观等等的判断,就像医生拿起解剖刀一样或者考古学家拿起铲子,一层一层很仔细地把它整理出来,这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
2022年,巫鸿的新作《豹迹:与记忆有关》。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做学术真的不允许个人的感情吗?我现在去看画,有时候还是会很激动,特别是看一些和自己的研究不那么重合的东西,比如我自己主要是研究中国艺术的,但是我会很有意识地常常去看西方的作品,从西方古代直到中世纪的东西我都很爱去看,而我不一定非要用学术来掩盖这种观看。比如《豹迹》里那篇《基督的血和玛利亚的泪》,就有一点在(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这二者之间了,它是由兴趣产生的一点研究性,但我还是自我控制,我从来没有把它写成学术文章;再比如我最近又去看庞贝,我对教堂、对西方现当代这些东西都非常有兴趣,在看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感觉就让它自动释放出来,但是我不一定要去分析这种感觉。所以在面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包括当代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还主要是艺术史学家的角色,还是在“研究”它们;但是在其他领域,比如在西方古代艺术或当代艺术面前,我希望能够保留那种对艺术的原初感觉。
所以《豹迹》就不太一样,我确实想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付诸文字,尝试能不能把研究的东西和个人的感觉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艺术”,就有点故意想用一种实验的方式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首先是把人称进行了转换,因为做历史研究的都是他者,不管是画家还是作品都是研究的对象和课题,传统上历史写作里比较忌讳的是使用“我”,当然现在也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用法来用,但是在《豹迹》里面,记忆就变成完全是“我”的感觉、“我”的冲动、“我”的失望……在这个状态下再去写石窟这些东西,就肯定很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我”不是一个恒定的东西,我写的这些“我”都是受地点或时间的控制,它是一个有点“vulnerable”(软弱)的“我”、一种感性的“我”,不是作为一个很坚定的学者去下结论的角色。所以在这种记忆里虽然写的还是美术品,包括那个蝉冠菩萨也是一个美术品,但它更多的是我和美术品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完全像艺术史学家那样去写,你完全做主导,而课题是被发掘、被解剖、被诊断和被研究。比如《豹迹》那篇其实就是从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变成了被眼前的东西给裹挟掉了,或者被你希望研究的东西给征服、给威慑住了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挺有意思。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实验性的,原来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的学术著作,那个“我”一直是隐藏的,而这本书希望能把这些方面体现出来,就像你说的好像内部通道一样,不是从外头看。所以《豹迹》不是给人展现一个宏大的结果,而是展示内部发生的一些更感性、更微小的东西。
H:那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实验状态下,被“软化”下来的不仅是写作的主体,还包括语言?因为这本书您是直接用中文来写的,而这种实验性的文本相较于学术著述中那种“坚固”的语言,也是一种松动,所以它也是中文艺术写作或者批评写作的一种实验。
W:一般在文学写作或者虚构性写作里,大家就比较自由,但是一旦牵扯到所谓“非虚构”,情况好像就变得很复杂,比如我怎么进入、或怎么表现这种写作者和对象之间的磨合关系就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次实验也是对于虚构和非虚构这种文体的分类所提出的一个问号,因为它和所有风格一样会构成分类,分类就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它本身是为了方便于一种约定俗成,但往往在方便之后就变原理性的东西了,变得很僵化。什么是写小说?什么是虚构?什么是历史学的东西?它成了一大套理论,而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灰色的地带。所以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玩,当时也有点调皮吧,我就想看你们将来把这本书往哪儿放了。我最近就看到一些书单子,它们都分成很多条目,而这本书好像真的就放不进去,但是看的人还蛮多的。你说它是历史类,也不是;文学类,它也不是,我倒觉得这是有点故意,至少让这个分类者觉得有点困难,有了困难就产生了问题,有了问题就需要解决。
巫鸿的家,能望见北美五大湖之一的密歇根湖,在那段因疫情而无法自由走动的时期,广阔的巨湖水面能让人平静下来。
H:在另一篇文章《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书》中,你提到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里读书和背书的那些经历,其中一段给我的触动很大,你说你到了哈佛后发现,虽然那些美国同学与你读过一样的书、看过一样的画、听过一样的音乐,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是通过学习而得到的历史,而对你来说却是“曾经经过的一段生命”。反观今天年轻的学者们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这种读书和生活、知识与生命之间的“内化”关联几乎很难再有,这可能也是大家现在在知识和研究中找不到实在感的一个原因,因为生活和研究被很清晰地割裂开来了。而《豹迹》这本书之所以能在研究者和回忆者的双重身份中来回切换并找到平衡,可能恰恰是因为这种知识和生命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你这里始终是非常紧密的。
W: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个人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人要求你去保存这些对艺术的感觉,大家的要求都是你要把研究、把那些职业化的东西做好,而原来所谓的那个初心其实是为了自己。当职业化之后,你的行动、思想都要按照职业的要求来做,成为学者和历史学家就是一种职业化,它并不要求你必须要对艺术增加多少感情。但是在所有这些职业化的要求之外,如果还能保持一个“人”的感觉,这种保存无论是对于你自己,还是对于生活、对于你周围的人,包括对艺术的向往,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决定。有人就觉得这个无所谓,或者在他那里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多少,也可以变成大学者,我觉得这对世界没什么损失,但是对他自己可能是一种损失。
当然像那些大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可能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还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有时候我也在想象这个东西,也可能我的年龄到这个份儿上了,原来确实是在职业化的路上走了很多年,但是另外的那部分,对于艺术的感觉或者这种敏感和喜好,还可以保留来。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多艺术史的书谈的不是艺术,它可能谈了这个画或者那个画家,但是那种谈是把它们作为一个“事情”、一个“东西”来谈,或者分析某种风格、这样的线那样的线,都是很客体化、科学化的,不牵扯个人对作品的感悟或者感动,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还能把它叫作艺术品吗?这里可能就有个问号。但如果你把它作为能够触动人、感动人的一种东西,这其实并不是艺术史研究里的职业要求。
所以我倒觉得不搞美术史的人可能对艺术接触能更多一点,真正职业化之后你反倒没有真正的自由去接近艺术作品原来的本质,就像音乐史家把音乐的每个小节都分开来分析,那么乐曲的整个旋律可能在他脑子里就消失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感觉。所以这两个东西之间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事。那篇书的记忆是源于我个人比较特殊的经验,它确实有一种超出科班训练的东西,但那是因为当时所有的训练体系都没有了,只能自己在外头乱碰乱找,很难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最后也可能留下点什么东西。
巫鸿觉得不搞美术史的人可能对艺术接触能更多一点,真正职业化后反倒没有真正的自由去接近艺术作品原来的本质。
H:保留下来的是那个完整的、大写的“我”,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在今天大多数高度职业化、技术化的领域里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大写化的东西了,所有都被细分了,都变成小写的了。而《豹迹》最触动我的地方就是让人看到了那个从严谨科学的研究工作中、从学科化的层层切片中往后退了一步的、大写的研究者和写作者的形象,这是特别难得的。
W:你确实看得比较仔细,《豹迹》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有点像个寓言,其中那个研究者可能是真的“我”。他有两面,一面是从开始就要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的人,要把那些艺术的东西都抛弃掉,因为只有科学记录才是有用的证据;而这一面到最后就被另一个“我”抛弃掉了,因为他被艺术的整体给笼罩了,那个学科训练的“我”在这时候就变得非常软弱和无能为力。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揭示了一种隐藏的矛盾,一方面你学术做得好,大家也说很好,看起来都很顺,好像没什么矛盾,因此在它下面的另一个“我”的声音就被隐藏、被消解掉了,而现在如果不是写学术的东西,就可以把这些隐藏的东西外化一下。这个故事虽然有回忆的成分,但是它在更深层上其实呈现了这种内在的矛盾——在职业化的东西和原始的艺术力量之间,或者也可以把这种力量看作是艺术本身拒绝被切割、拒绝被解剖。它最后可能是胜利了,所以这里有一种艺术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既是分析者,也是艺术的欣赏者。
上图、下图:在巫鸿位于芝加哥的家中拍摄时,我们发现了这些铁皮机器人,对巫鸿来说,这是已持续了二三十年的“轻松收藏”,从不刻意,却也形成了一支小队,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上方的“白纸”其实是艺术家刘建华的陶瓷作品,极简、东方的意味和下方热闹、童趣的机器人形成对照,向我们透露了学者形象之外的巫鸿。
H:如果把《豹迹》和你年初出版的学术著作《空间的敦煌》放在一起看,就更加能够理解你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身体经验、对于一种移步换景的空间体验的重视。你总是能够从一种生命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和写作,包括为记忆所找到的那种非常具体的、视觉化的渊源。那么你在写作《豹迹》的过程中,是如何具体地处理这种记忆的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
W:是,我觉得这大概有两方面:《空间的敦煌》是谈艺术品,《豹迹》也是与时空有关,这就牵涉到不但是观看,也包括做学问的方法问题。当然美术史研究是从视觉出发的,你必须要“看”,包括训练学生怎么看,然后把“看”转化为文字,这是美术史学科的一个核心和基础。如果做文学史、哲学史,就不一定要有这种转化,还是从文字到文字。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转化其实运用得并不是很好,很多艺术史的书其实并没有显示出这种转化,还是从文字材料出发的,因为大家还是觉得文字作为历史证据是最权威的,文字会告诉你有什么人、有什么精确的事件,而美术品自己没法说这些事。
在《空间的敦煌》里,你提到移步换景、层层进入,这是因为空间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它引导我们把敦煌艺术重新“原境化”(contextualized)。而且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身体,因为很多东西比如多大、多小,都是身体的感觉,这些东西需要在艺术史的写作里把它做成一个很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运用的基础性方法论。所以《空间的敦煌》里五个章节的结构就是从最大的空间——整个敦煌地区的空间再一步步缩小,最后落到一张画的空间,到结论我就写了一个很清楚的方法论。所以你刚才说到的那种对艺术品的生命体验和我的感觉是一致的,因为我特别强调的东西不是要先去看书或者知道很多历史背景,而是说不管是绘画、雕塑、石窟,它首先是一个关乎感觉的东西,它的逻辑在哪里?你必须用眼睛,包括身体,尤其像雕塑这样的东西,把它的逻辑性——视觉的逻辑性、空间的逻辑性等等,感受出来,再呈现出来,然后结合文献的二手资料。我觉得我从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特别希望能够继续。
《空间的敦煌》插图:莫高窟第328窟佛龛,7世纪。
回到最早写的那本《重屏》,其实就是用这种方法,把中国绘画想成一个物质性、中间性的东西。我也写了很多关于手卷的东西,这是中国艺术对世界艺术最大的贡献之一,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静止在画框里的那种绘画,而是一直在运动中、有时间性的,就像古代的电影一样,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结合体,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谈得太少了;而且手卷里有那么多种实验,比如怎么控制节奏,怎么来确定帧格,都很复杂,所以有时候我们系里教电影史的学者也用这本书去教学生。但是这些东西原先研究得不够,缺乏文字性的叙述,古代也没有什么文献去真正探索,因为它已经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个固有的东西,就反而不谈了,变成一种“default”(默认)的东西,一种作为语言本身的很自然的存在,所以古代人也不谈中国画的语言是怎么样,很少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default”。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研究应该回到这种非常根本的东西,因为美术的很多根本性问题就是关乎视觉和媒材的。这种对于视觉空间经验的重视,在我看来对任何艺术品、任何建筑来说,不管是学术性的研究还是个人欣赏,都是第一位的。而且它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长着眼睛都能看见,“看见”和“会看”是两回事,就像文盲也会“看见”这本书和字,但是他不会念。所以我也给类似的情况起了个名字叫“视盲”,就是你也能看见这些,但是你说不出来,因为你对它的视觉逻辑、识别语言完全不懂。有时候教大学生往往就是要解决“视盲”的问题,教他们怎么使用一个形象把它转换为一种证据,因为形象是一种知识,但是你不分析,它就不是知识,它只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存在,你要把它变成可以用的知识,就必须会分析,从“视盲”到可以操作这种视觉形象需要一个转化。
H:你刚刚提到一句话,“还是要相信身体”,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这其实都不太像是艺术史学家会说出来的一句话。
W: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太基本,但其实身体太重要了。包括我在谈手卷里也谈到它为什么叫手卷,因为你总得拿手去碰触它,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和画是连着,而西方艺术史有哪种画是与身体连着的呢?没有。当你画画和做雕塑的时候有,但是观赏的时候它已经是分开的了,所以西方艺术史很多时候是在建立完全客观化的东西,比如所谓的透视就是把绘画作为一个客体,要去创作一个客体的“illustion”(幻象),而中国画的手卷是连成一体的,而且只有一个人能看,就由他来掌握这个东西。所以身体太重要了,不仅是手卷,还包括立轴、屏风等等,我们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做,在概念上再进行挖掘。这些当然是比较学科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和个人那种对艺术的敏感是连着的,如果你这个人完全没有这种对艺术品的敏感,就可能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虽然不一定把自己的感觉都带进来,但是这种对于艺术品的承认要有,而且要仔细地去感受,不但用眼睛,还要用身体去感受、去想,这种感受本身就含有一种知识性的东西,这部分其实可以移到学术研究中去。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些会让人感觉不是什么美术史的问题,比如对敦煌艺术来说为什么空间那么重要,当我进入一个窟,特别黑,这个“黑”在传统的美术史论里会觉得很不幸,因为太黑了看不清,但对我来说这个“黑”就是当时视觉经验的一部分,观者从外面很敞亮的空间进入里面一个很黑的窟室,那为什么是石窟?为什么不开一个很敞亮的厅呢?它肯定有它的意义,钻进这种山体的内部是完全不一样的空间。所以在这种“黑”里面去发现那些非常神奇的作品,它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就存在石窟,还有在法国拉斯科洞窟里那些最早的壁画,以及从柏拉图所说的“cave”(山洞、洞窟)到中国的这些石窟——但关于“什么是石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确实的回答。大家可能去研究里面的作品是什么风格、什么年代,但是“What is cave? Why cave?”(什么是石窟?为什么是石窟?)。石窟有一套它的视觉语言,它只有内部空间,没有外在空间,不像独立的建筑那样可以转着看它的外在形状,窟只有一个门脸儿,没有一个外在形象。这些东西都很值得研究,将来有时间我也会谈,但是我觉得它们都牵扯到身体和艺术品的关系,需要重新去以一种很基本的结构来思考。
《豹迹》插图:巫鸿与木心在哈佛大学,1984年。
H:在《豹迹》最后一篇《木心的记忆》里,你提到希望放弃历史化的、专业分析的方法去写木心,反之采用了另一种看似不去甄别事实和虚构的手法,以“非历史的形象”去发现一个“真实”的木心。这就涉及到如何写“史”、写“批评”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将它界定为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写作方法。那么你认为这种手法是专门针对于写木心这一特殊的个案,还是说它可以被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批评写作手法,即使是作为实验性的?
W:这个问题大概有这两层。一是我们写作历史到底要写哪一层?原先有一种理解就是一定要发掘到所谓历史的真相,而研究就是要发现它背后的东西。所以这篇文章也不光是你说的反美术史,而是说对历史写作本身是否能提出另外一种写法?倒不是说要完全取代原先的那种东西,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各种写作都有它的用处。那么就这种方法而言,如果这个被写的对象,他那种很强的创造力是在创造一个艺术品的“我”,或者说把创造一个“person”(形象、人物)——这个“我”变成他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很多时候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好像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作品本身的意义,另一个是所有这些作品所构造的一种艺术性的“author”(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想去发掘这个艺术建构性的“作者”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人其实在这个“作者”本人看来并不是作品的真正作者,而就是一个物质性的人。对我来说,创作者到底怎么去建构这个“作者”可能是最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关于木心当时到底在地窖里住了多少天,这个地窖是怎么样的等等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说,那我何苦去挖这些东西,即使挖出来,也未必对他的这种(艺术性的)自我建构有意义。
从另一层来讲,为什么说这种写作方法也可能是广义的呢?咱们都学过后现代理论,就是什么东西都是“constructive”(建构性) 的,包括我们看的所有历史作品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都是建构起来的东西。司马迁就有很强的“我的”概念,在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他会写自己如何遭受宫刑等等,所以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外化。很广义地来说,可以从这个作品或者作者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这个层次上来理解,而不是考古式地去发掘作者背后的东西,就是把这种建构性的东西看作是一个现实,它就是现实本身——这个线索我觉得对于艺术来说更有意思,它和专门做实证性的历史还不一样,艺术史或文学史,作品本身就是要研究的对象,它可能更重要,我也是因为通过木心的作品就开始想这些问题。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我们在耶鲁大学给木心做的一个展览上,后来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看了特别喜欢,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对这个东西很敏感,说这样看历史确实很不一样,不是我们假设历史一定要找那个真实,而是要把历史上这些人——他的愿望、他的自主性,就是他要干什么,把这些东西承认下来,这也是一种共情(sympathy)。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不是把历史的问题都当作材料,它还是有它的主体性的,这个主体性本身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怎么化为艺术,怎么化为文字。所以每个艺术家之不同,可能就在这个层面上,他怎么把自己转化为作品,或是通过作品来建构自己,这可能是一种想法。
巫鸿策展物之魅力:当代中国“材质艺术”现场。朱金石《物的浪》,2007。
H:除了学者,你还有一个常见的身份是策展人。你刚才提到艺术史学家要学会“看”,从视觉材料出发,将这种专业的“看”转化成为文字,而学者做策展,这个工作又需要另一重转化,把文字再次转化为一种视觉呈现。作为观众,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学者为什么要做展览?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去读这个学者的书、看他编辑的展览图册,或许能收获比展览更多的东西?
W:首先,为什么要做展览?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要做展览。对我来说,第一是个人兴趣,我小时候就喜欢艺术,也画了很多年画,所以和艺术家打交道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有时候也不是非要做展览,谈一谈就很好。所以做展览是和艺术品本身、艺术家本人的接触,它还没有被转化为文献、照片或者资料,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事,它和写书不一样,主要是要作品本身去说话而不是通过文字去叙述。第二是对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的部分是把展览空间布置好,即使美术馆有自己的设计者,展览的空间设计我还是参与得非常多。这个展览如何进入、怎么看,这个空间的逻辑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这也是一种满足。展览的空间不是完全知识化的空间,而是一个很具体的空间。
展览的吸引力还有一点,就是它和书特别不一样,这些东西会消失。所以在我的展览和我的写作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关系,在比较大型展览上,我也都有像写书一样的那种投入,当然书和展览又不能完全一样,各自梳理的是什么,这两个东西之间应该有一种对话的感觉,最后这个展览消失了,书留下来了,消失本身就有点惆怅,这也是很真实的一种感觉。
采访:贺婧
摄影:Nolis Anderson
编辑:吴亦飞
排版:王子涵、Anya